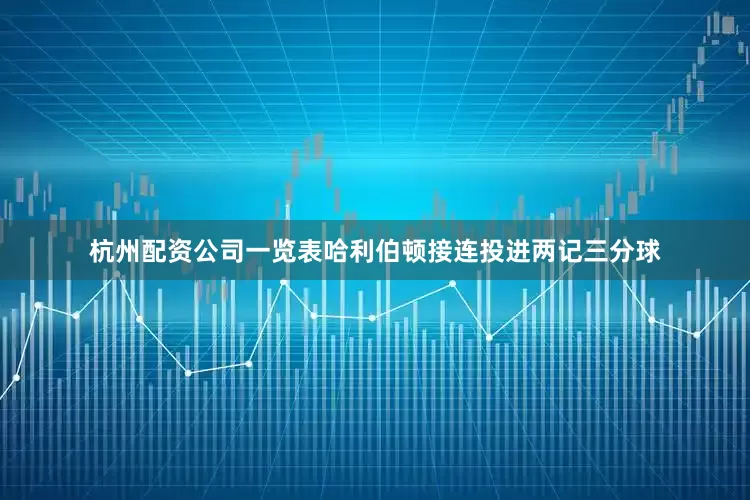图片
天行有常,不为尧存,不为桀亡。应之以治则吉,应之以乱则凶。强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,养备而动时,则天不能病;修道而不贰,则天不能祸。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,寒暑不能使之疾,袄怪不能使之凶。
自然界的运行有其恒常的规律,不会因为尧的圣明而存在,也不会因为桀的暴虐而消亡。用合理的措施去顺应它就会吉祥,用混乱的措施去对待它就会遭殃。加强农业生产且节约用度,那么天也不能使人贫穷;衣食充足且活动适时,那么天也不能使人患病;遵循道义而坚定不移,那么天也不能使人遭祸。所以,水旱灾害不能使人挨饿,严寒酷暑不能使人生病,自然怪异不能使人凶险。
本荒而用侈,则天不能使之富;养略而动罕,则天不能使之全;倍道而妄行,则天不能使之吉。故水旱未至而饥,寒暑未薄而疾,袄怪未至而凶。受时与治世同,而殃祸与治世异,不可以怨天,其道然也。故明於天人之分,则可谓至人矣。
反之,如果农业荒废且用度奢侈,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富裕;衣食不足且活动稀少,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健康;违背道义而胡作非为,那么天也不能使人吉祥。于是,水旱灾害没有到来就会挨饿,严寒酷暑没有逼近就会生病,自然怪异没有出现就会凶险。所遇到的天时与治世相同,但遭受的灾祸却与治世大异,这不能够埋怨上天,是人的行为方式造成的。所以,明白了自然与人的分际,就可以称为至人了。
不为而成,不求而得,夫是之谓天职。如是者,虽深,其人不加虑焉;虽大,不加能焉;虽精,不加察焉: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。天有其时,地有其财,人有其治,夫是之谓能参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,则惑矣。
不用人为就能完成,不去寻求就能得到,这叫做自然的职能。像这样的事情,即使道理深奥,那至人也不会去多加思虑;即使影响广大,也不会去多加干预;即使道理精妙,也不会去多加考察:这就叫做不与自然争夺职能。天有它的时令季节,地有它的资源财富,人有他的治理方法,这就叫做能够与天地相互配合。如果舍弃人自身能够配合天地的努力,却一味寄希望于天地本身,那就是糊涂了。
列星随旋,日月递照,四时代御,阴阳大化,风雨博施,万物各得其和以生,各得其养以成,不见其事而见其功,夫是之谓神。皆知其所以成,莫知其无形,夫是之谓天。唯圣人为不求知天。
星辰旋转,日月交替照耀,四季轮流主宰,阴阳二气化生万物,风雨普遍施与,万物各自得到自然的和谐而生长,各自得到自然的滋养而成熟,看不见它们是如何工作的,却能看到它们的功绩,这就叫做神奇。世人都知道万物生成的样子,却不知道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,这就叫做天。只有圣人不强求去了解那神秘莫测的天。
天职既立,天功既成,形具而神生,好恶、喜怒、哀乐臧焉,夫是之谓天情。耳目鼻口形能,各有接而不相能也,夫是之谓天官。心居中虚以治五官,夫是之谓天君。财非其类,以养其类,夫是之谓天养。顺其类者谓之福,逆其类者谓之祸,夫是之谓天政。
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,自然的功绩已经成就,人的形体具备而精神随之产生,好恶、喜怒、哀乐等情感都蕴藏其中,这就叫做自然的情感。耳朵、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身体,各自有接触外物的功能而不能互相替代,这就叫做自然的感官。心居于胸腔之中来管理五官,这就叫做自然的主宰。利用自然界的万物来供养人类,这就叫做自然的养育。能顺应人类需求的叫做福,违背人类需求的叫做祸,这就叫做自然的政令。
暗其天君,乱其天官,弃其天养,逆其天政,背其天情,以丧天功,夫是之谓大凶。圣人清其天君,正其天官,备其天养,顺其天政,养其天情,以全其天功。如是,则知其所为,知其所不为矣,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。其行曲治,其养曲适,其生不伤,夫是之谓知天。
如果蒙蔽了自然的主宰,扰乱了自然的感官,废弃了自然的养育,违背了自然的政令,背离了自然的情感,从而丧失了自然成就的功绩,这就叫做大凶。圣人则澄清自己的心智,端正自己的感官,完备自然的供养,顺应自然的政令,调养自然的情感,以此来保全自然成就的功绩。像这样,就知道什么是应该做的,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了,那么天地都能被掌管而万物都能被役使了。他的行为处处都合理,他的供养处处都恰当,他的生命不受伤害,这就叫做真正了解了天。
故大巧在所不为,大智在所不虑。所志於天者,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;所志於地者,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;所志於四时者,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;所志於阴阳者,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。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。
所以,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,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。对于天的认识,是根据它所显现的天象来预测变化;对于地的认识,是根据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来安排繁殖;对于四季的认识,是根据它们所显现的节律来安排农事;对于阴阳的认识,是根据它们所显现的和谐状态来治理事务。让专人掌管观察自然现象,而圣人自己则坚守治理人世的大道。
治乱天邪?曰:日月、星辰、《瑞历》,是禹、桀之所同也,禹以治,桀以乱,治乱非天也。
国家的治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?回答说:日月星辰、历象节令,这些自然现象在圣君大禹和暴君夏桀的时代都是相同的。然而,大禹使天下安定,夏桀却使天下大乱。由此可见,国家的治乱并非由上天决定。
时邪?曰:繁启蕃长於春夏,畜积收臧於秋冬,是又禹、桀之所同也,禹以治,桀以乱,治乱非时也。
是由四季时令造成的吗?回答说:万物在春夏季节萌芽、生长、繁茂,在秋冬季节收获、储藏、积累,这种自然规律在大禹和夏桀的时代也是相同的。大禹借此实现了大治,夏桀却招致了祸乱。所以,国家的治乱并非时令造成的。
地邪?曰:得地则生,失地则死,是又禹桀之所同也,禹以治,桀以乱,治乱非地也。
是由土地条件决定的吗?回答说:拥有土地万物就能生长,失去土地万物就会消亡,这个道理对大禹和夏桀也是相同的。大禹用它开创了治世,夏桀却导致了乱世。因此,国家的治乱也并非土地决定的。
《诗》曰:“天作高山,大王荒之,彼作矣,文王康之。”此之谓也。
《诗经》上说:“上天生成高高的岐山,太王(古公亶父)苦心经营它;他奠定了基业,文王又使它安定繁荣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,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,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。天有常道矣,地有常数矣,君子有常体矣。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。《诗》曰:“何恤人之言兮!”此之谓也。
上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废止冬天,大地不会因为人们厌恶遥远就缩小面积,君子也不会因为小人的喧哗反对就停止自己的正道之行。上天有其恒常的规律,大地有其不变的法则,君子也有其坚守的行为准则。君子遵循其恒常的准则,而小人则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功利。《诗经》中说:“何必顾虑别人的闲言碎语呢!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楚王后车千乘,非知也;君子啜菽饮水,非愚也:是节然也。若夫心意修,德行厚,知虑明,生於今而志乎古,则是其在我者也。
楚王出随从的马车多达千辆,并非是因为他聪明;君子吃豆粮、喝白水,也并非是因为他愚笨;这都只是机缘时运造成的偶然情况。至于思想端正、品德高尚、谋虑精明,生在当今之世而心志追慕古代的贤人,这些则是取决于我自己努力的事情。
故君子敬其在己者,而不慕其在天者;小人错其在己者,而慕其在天者。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,是以日进也;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,是以日退也。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,一也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。
所以,君子严肃认真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身的事情,而不去仰慕那些由上天命运决定的事情;小人则舍弃那些取决于自身的事情,去仰慕那些由上天命运决定的事情。正因为君子严肃对待自身的事情而不仰慕天命,所以每天都不断进步;小人因为舍弃自身的事情而仰慕天命,所以每天都不断退步。君子之所以日益进步和小人之所以日益退步,原因是一样的。君子和小人之所以相差悬殊,原因就在这里了。
星队、木鸣,国人皆恐。曰:是何也?曰:无何也,是天地之变,阴阳之化,物之罕至者也,怪之可也,而畏之非也。
流星坠落、社树发声,全国的人都感到恐惧。有人问:这是怎么回事?回答说:这没有什么,这只是天地的常规变动、阴阳二气的正常转化,是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。觉得它奇怪,是可以的;但害怕它,就错了。
夫日月之有蚀,风雨之不时,怪星之党见,是无世而不常有之。上明而政平,则是虽并世起,无伤也;上闇而政险,则是虽无一至者,无益也。夫星之队,木之鸣,是天地之变,阴阳之化,物之罕至者也,怪之可也,而畏之非也。
日食月食的发生,狂风暴雨不合时节的突然袭击,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,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。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,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,也没有什么妨害;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,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,也毫无裨益。那些流星的坠落、树木的发响,确实是天地阴阳的变化中罕见的现象。觉得奇怪,是可以的;但害怕它,就错了。
物之已至者,人袄则可畏也。楛耕伤稼,耘耨失岁,政险失民,田薲稼恶,籴贵民饥,道路有死人,夫是之谓人袄。政令不明,举错不时,本事不理,夫是之谓人袄。礼义不修,内外无别,男女淫乱,则父子相疑,上下乖离,寇难并至,夫是之谓人袄。
在已经发生的事物中,真正值得畏惧的,是“人祅”(即人为的灾祸)。粗劣的耕作伤害庄稼,马虎的锄草影响收成,政治险恶失去民心,以致田地荒芜、庄稼歉收,米价昂贵百姓饥饿,道路上有饿死的人。这就叫做人祅。政策法令不明确,国家举措不合时宜,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。如果征发劳役不顾农时,那么牛马就会生出怪胎,六畜就会出现反常现象。这也叫做人祅。礼义不加整顿,家庭内外没有界限,男女关系淫荡混乱,以致父子互相猜疑,君臣离心离德,外患内乱同时到来。这同样叫做人祅。
袄是生於乱,三者错,无安国。其说甚尔,其灾甚惨。勉力不时,则牛马相生,六畜作袄,可怪也,而不可畏也。
这些人为的灾祸都源于社会政治的混乱。如果上述三类人祸交错发生,国家就不得安宁。这个道理说起来很浅近,但它们带来的灾难却异常惨重。至于那些因为征发劳役违背农时,而导致的牛马生出怪胎、六畜出现反常等现象,这些可以觉得奇怪,但并不可怕。
传曰:“万物之怪,书不说。无用之辩,不急之察,弃而不治。”若夫君臣之义,父子之亲,夫妇之别,则日切瑳而不舍也。
古书上说:“人间的各种怪现象,经书是不作解说的。”没有用处的辩说,并非急需的考察,应该抛弃不去研究。至于君臣之间的道义、父子之间的亲情、夫妻之间的区别,则应该每天深思钻研,而不能有丝毫懈怠。
雩而雨,何也?曰:无何也,犹不雩而雨也。日月食而救之,天旱而雩,卜筮然后决大事,非以为得求也,以文之也。故君子以为文,而百姓以为神。以为文则吉,以为神则凶也。
举行求雨的祭祀仪式后就下雨了,这是为什么呢?回答说: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,就和没有举行祭祀仪式也会下雨一样。出现日食月食便去抢救,遇到天旱便去祈雨,通过占卜然后决定重大事项,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真的能祈求到什么结果,而是用来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文饰。所以,君子将这些活动视为一种文饰,而老百姓则把它们看作是神灵之事。把这些活动当作文饰(以引导和教化百姓)就会带来好处;但如果真的相信它们有神灵之力,那就会招致祸患了。
在天者莫明於日月,在地者莫明於水火,在物者莫明於珠玉,在人者莫明於礼义。故日月不高,则光晖不赫,水火不积,则晖润不博;珠玉不睹乎外,则王公不以为宝;礼义不加於国家,则功名不白。
在天上的东西,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;在地上的东西,没有比水火更明亮的;在万物中,没有比珠玉更明亮的;在人类社会中,没有比礼义更明亮的。所以,日月如果不高悬空中,它们的光辉就不会显赫;水火如果不积聚,它们的光辉和润泽就不会广博;珠玉的光彩如果不显露于外,王公贵族就不会把它当作宝物;礼义如果不施行于国家,那么它的功业和名望就不会显扬。
故人之命在天,国之命在礼。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,重法爱民而霸,好利多诈而危,权谋、倾覆、幽险而尽亡矣。
因此,个人的生命取决于如何对待自然(即遵循规律),国家的命运则取决于是否实行礼义。统治人民的君主,尊崇礼义、敬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,重视法度、爱护百姓就能称霸诸侯,贪图私利、多行欺诈就会陷入危险,玩弄权术、搞颠覆、阴暗险恶就会彻底灭亡。
大天而思之,孰与物畜而制之?从天而颂之,孰与制天命而用之?望时而待之,孰与应时而使之?因物而多之,孰与骋能而化之?思物而物之,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?愿於物之所以生,孰与有物之所以成?
与其推崇上天而思慕它,何如将天当作物质资源来畜养并控制它?与其顺从上天而歌颂它,何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?与其盼望天时而等待恩赐,何如因时制宜而驱使它?与其听任万物自然增多,何如施展人的才能去改造它?与其空想万物为自己所用,何如治理万物而不失去它们?与其寄希望于万物自然生长,何如参与促进万物的成长?
故错人而思天,则失万物之情。
所以,如果放弃人的努力而一味地仰慕上天,那就违背了万物的本性和情理。
百王之无变,足以为道贯。一废一起,应之以贯,理贯不乱。不知贯,不知应变,贯之大体未尝亡也。
历经百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,足以成为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。朝代有衰亡有兴隆,但都要用这个根本原则去应对。用这个原则来治理,国家就不会混乱。如果不了解这个根本原则,就不知道如何应对变化。但这个原则的主体是永远不会消亡的。
乱生其差,治尽其详。故道之所善,中则可从,畸则不可为,匿则大惑。
天下大乱,是因为运用这个原则时出现了偏差;天下大治,则是因为将这个原则周详彻底地贯彻了。所以,以“道”为标准来衡量,行事适度就可以遵从,偏离正道就不可行,完全违背就会导致极大的迷惑。
水行者表深,表不明则陷;治民者表道,表不明则乱。礼者,表也。非礼,昏世也。昏世,大乱也。
涉水的人依靠标志来探测深度,如果标志不明确,就会沉溺溺水;治理百姓的君主,要以“道”作为标准。如果标准不明确,国家就会混乱。“礼”就是治理国家的这个标准。违背了礼,就是昏暗的时代。昏暗的时代,必然是大乱的时代。
故道无不明,外内异表,隐显有常,民陷乃去。
所以,“道”的各个方面没有不明确的,它对内外之事有不同的标准,对隐微和明显的行为都有恒常的规定,这样,百姓的灾祸就可以免除了。
万物为道一偏,一物为万物一偏,愚者为一物一偏,而自以为知道,无知也。
万事万物都只是“道”的一个方面,一种事物又是万事万物的一个方面。愚蠢的人只认清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,就自以为懂得了“道”,这实在是太无知了。
慎子有见於后,无见於先;老子有见於诎,无见於信;墨子有见於齐,无见於畸;宋子有见於少,无见於多。
慎子(慎到)只看到了后发制人、循名责实的一面,而没有看到积极引导、率先垂范的一面;老子只看到了委曲求全、以柔克刚的一面,而没有看到积极进取、有所作为的一面;墨子只强调普天之下一律平等的一面,而忽视了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等级差异的一面;宋子(宋钘)只看到人的欲望寡少的一面,而忽视了人也有正常且多样的欲望需求的一面。
有后而无先,则群众无门;有诎而无信,则贵贱不分;有齐而无畸,则政令不施,有少而无多,则群众不化。
只讲后发制人而不讲率先引领,那么群众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门径;只讲屈从退让而不讲伸张进取,那么贵贱之间的等级就无法区分;只讲绝对平等而否定差异,那么政令就无法推行(因为赏罚无法实施);只承认欲望寡少而否认欲望众多,那么群众就得不到教化引导。
《书》曰:“无有作好,遵王之道;无有作恶,遵王之路。”此之谓也。
《尚书》上说:“不要凭个人的喜好行事,要遵循先王的大道;不要凭个人的厌恶行事,要遵循先王的正路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股票金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手机炒股好用的选哪款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
- 下一篇:没有了